电子工业遗产及其价值——以显示工业为例
时间: 2025-07-16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
摘要:20世纪中叶,工业遗产开始受到社会关注。几乎在同一时期,电子工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其产线世代更迭远比人类世代更迭迅速,因此,对于其是否构成文化遗产,不应以传统的“完成人类代际传递”作为衡量的必要条件。显示工业是我国电子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有其独特性和代表性,从科技史和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显示工业及其遗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明晰其本土化发展进程,阐释其遗产价值。 关键词:显示工业;工业遗产;文化遗产;年代价值;技术价值
一、
概论
1. 工业革命与工业遗产
18世纪后半叶发起的工业革命,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持续的创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导致其技术和空间不断革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即产生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不仅包含车间、矿场、机械设备,还包含与工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以及其它能够集中承载工业文化的历史遗存。常见的工业遗产类型,有矿冶采炼遗址,如瑞典恩格尔斯堡铁矿工场(Engelsberg Ironworks);有工业生产相关的历史市镇,如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历史市镇中心(Historic Centre of Zacatecas),还有作为基础设施的铁路、运河、桥梁,如印度大吉岭的山区铁路(Mountain Railways of India)。由于遗存本体的年代相对晚近,直至上世纪中叶,在英国、日本等国学者的持续努力下,工业遗产才开始受到学界、社会的关注,远远晚于其它类型的文化遗产。
1955年,英国伯明翰大学迈克尔·里克斯(Michael Rix)基于工业考古学理论,率先涉足“工业遗产”概念[1]。1986年,英国铁桥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收录的第一项工业遗产,正式标志着工业遗产成为国际共识下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2000年后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发布《下塔吉尔宪章》[2]等文件,进一步奠定了工业遗产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最初集中出现在本世纪初,始于对英、德等国工业遗产旅游相关案例和理论的引介。近二十年来,学界的研究热情持续升高,然而,相对于其他遗产类型,工业遗产受到的关注仍然较少,相关理论框架仍待进一步完善。
2. 电子工业与电子工业遗产
与此同时,工业本身也在以越来越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其中,电子工业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以集成电路和液晶平板显示为例,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3]指出,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提升一倍;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亦提出液晶显示行业的“生存定律”[4],即,液晶显示面板的产品性能和有效技术保有量需每三年提升一倍以上。从具体产线的使用年限来看,其更新速度确实远快于其它工业类别,以韩国三星为例,其第一条五代线①于2002年投产,2015年停产,历时13年;其第一条七代线在五代线后3年(2005年)投产,2016年停产,历时11年,可见产线世代更迭之迅速。
当前普遍认为文化遗产需满足“完成人类代际传递”这一条件,其存续时间应至少大于30年。[5]以与工业遗产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建筑类文化遗产为例,认定的最低年限多在30年至50年不等,如上海颁布认定的“历史建筑”的最低年限为30年,[6]又如美国“国家登录制度”(National Register)则一般要求其存续时间在50年以上。[7]考虑到一般功能建筑的使用年限,这样的设定是合理的,然而,电子工业的代际更迭要远快于30年——按“摩尔定律”、“生存定律”以及实际产线升级的情况来看,30年的时间足以覆盖电子工业10代的代际传递,原有的文化遗产衡量标准并不适用于这个高速发展变化的产业类型,如果我们仍旧以上述相对“普适”的概念来衡量这些电子工业遗产,难以公平界定其遗产本体,更难以客观阐释其具有的遗产价值。
与之相对的,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相关产业越来越快的更新速度,意味着大量的电子工业遗产在我们对其进行客观认识、评价之前,就已经被废弃、损毁。由于年代晚近,电子工业遗产当前所处的境地十分尴尬,不仅在社会上缺乏关注度,学界也缺乏相关讨论——当前对于工业遗产的学术讨论,大多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前,尤以“三线建设”、“156工程”为主。具有官方性质的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名录”,[8]其评定的时间下限也定在了1980年——大量的电子工业始建年代都要晚于这一时间节点;而由文博部门主导的对于相关遗存的认定,其时间下限甚至还要更早。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子工业遗产似乎已经被排除在当前官方话语体系之外。
中国在工业化史的进程上来看较慢,但是在世界工业史和创新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定位,[9]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进程就有其独特性和代表性。在这一背景下,客观地认知、阐释中国电子工业遗产的价值,将它们及时纳入到文化遗产的范畴之中,才有可能避免这部分见证工业发展重要进程的遗产被继续忽视、损毁,才有可能建立科学认知,进而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展示与利用。
电子工业的类型很多,各类型在发展历程和工艺流程上差别较大。其中,显示工业具有高速发展、替换前代、依赖生产这三项电子工业显著特征,是我国电子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选择显示工业作为主要讨论对象,试明晰其本土化发展进程,阐释其遗产价值。
二、
显示行业的发展概况、产线更迭与遗产形成
1. 显示器件的技术背景与本土发展概况
显示器件(Display Device),即人机界面(Man-machine Interface),指将各种电子装置输出的电气情报信息变换为人的视觉可辨知的光情报信息的器件。[10]最早的显示器件是阴极射线管(CRT)显示器,其关键技术在1897年由布劳恩攻克,在20世纪上半叶即开发出基于CRT的前端显示器。直到2000年前后,CRT一直是最为主流的显示器件,被成熟应用于多个领域。
打破CRT垄断地位的是液晶显示。上世纪60年代末,瑞士的两位科学家马丁·斯凯特(Martin Schadt)和沃尔夫冈·海佛里奇(Wolfgang Helfrich)发明了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器(TN-LCD),奠定了LCD商业化的核心基础。[11]此后,液晶显示器经历了从无源到有源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今天以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为主的液晶显示产业。由于TFT-LCD显现出的平板化、便携性、稳定性以及规模化效应所带来的价格优势,逐步击败了等离子显示(PDP)、场致发射显示(FED)等竞争对手,成为继CRT之后的新一代主流显示器件,其产业规模已近千亿美元级。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显示行业的发展进程,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78至2007年前后CRT占据主流的阶段和2007年以来由TFT-LCD占据主流的平板显示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彩电“技术引进”的大门重启,久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释放,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全国各地的CRT彩电工业迅速发展。自1978年中央决定引进第一条国外生产线开始,到1985年国务院发文严禁各地继续引进彩电整机生产线为止,八年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整机生产线。此后,中央调整“技术引进”策略,由原先的整线引进、进口彩管和元器件,调整为建立除核心芯片之外的完整的CRT电视产业链,在1985至2000年间,又引进彩电配套电子元器件生产线近300条。1978年以来的大规模引进、建设CRT整机及相关产线,曾经是中国依靠“技术引进”发展电子工业的正面典型案例,但这一典型的树立,忽略了电子行业,或者说电子显示行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快速的技术更迭;一项关键技术的出现,会替换前代技术及其制造业体系,而这一过程相较于传统工业更加迅速且全面。
2. 产线更迭与遗产形成
如前文所述,自1980年代开始,CRT已经显现出它在便携性上的巨大缺陷,但因为当时的LCD技术尚未成熟应用至大尺寸前端显示器件中,CRT的需求量仍然平稳增长,一旦两方僵持至零界点,TFT-LCD就迅速占领了市场。以彩电为例,平板显示彩电从2003年在国内市场初露端倪,至2009年在销售量上决定性地超过CRT彩电,[12]前后不过短短6年。又由于它本身是一种由半导体控制的显示TFT,半导体技术的巨大潜力又加持了TFT-LCD的发展潜能,在其自身的世代替换上,也极为快速。以玻璃基板的尺寸为衡量因素来看,1990年日本启动了第一条彩色TFT-LCD量产线即一代线,至2004年出现第一条高世代线六代线,间隔14年时间,而从六代线发展到目前最大尺寸的十点五代线仅用了5年的时间。原有较低世代线的生产空间往往不能满足后续的生产需求,更新、更高的世代线大多重新选址建厂,而新的大尺寸前端显示产品的出现,又使得对于原有小尺寸玻璃基板的需求量锐减。这一过程中,原低世代厂房的属性和价值发生了转变,与已经边缘化的CRT整机及元器件生产厂房一样,它们失去了其原有的生产功能,被废弃、改造甚至拆除,但如果在工业遗产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以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又被赋予了新的价值。
三、
显示工业的特点
对应本文主要讨论的文化遗产领域,显示工业的特点主要有三。
1.技术更迭迅速
电子工业的技术发展和产线换代远比其他工业迅速,而相较于其它类型的电子工业,电子显示工业在其中又更为突出。如,以半导体行业为参照,平板显示技术的变化率在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就超过了半导体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变化率,即TFT-LCD的制造商在不到一半的时间里就会经历半导体工业一个世代线的变化。[13]这种更迭速度是很多其它产业类型难以企及的,以茶业为例,经过历史时期数千年的茶树驯化和制茶工艺改良过程,在1860年以后伴随着揉捻机和烘干机等技术发明和流程改进,现代制茶工业才在印锡诞生。因此,也必不能使用同一划定标尺来衡量显示工业遗产的年代价值。
2.对生产空间的要求高,依赖性强
显示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都离不开新的生产设施,而生产设施的变更往往也要求重新组织生产空间,这一点在平板显示工业中更为明显——更大尺寸的显示屏只能由更高世代的生产线生产出来。尺寸的增长要求重大的工程设计变动,高世代生产线要求的空间尺度和组织方式,往往不能在低世代生产线的生产空间中满足。因此,一条新的更高世代的生产线,不仅意味着新开发的生产设备,还意味着新修建的生产空间(厂房及其附属空间),以及,意味着一部分原有低世代生产空间和设备终止了其原有的生产功能,改为它用或废弃、拆除。
举例来说,一条四点五代的TFT-LCD产线及配套设施占用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具有代表性的主设备区域需要的最小层高4.6米;一条六代产线及配套设施占用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主设备区最小层高6.5米;到十点五代线时,数字分别达到了89万平方米和9.6米,所需面积是四点五代线的十倍有余,层高需求也已经翻倍,原有的生产空间显然无法满足。
3.发展进程、产业布局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中国显示工业的发展,与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导向息息相关,此处以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停滞、1973-1974年的“蜗牛事件”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技术引进”三个典型时段/事件来举例说明。[14,15]
1960年代的技术停滞。我国的显示工业起步并不晚,在1956年制定的中国“十二年科技计划”中,电子工业中的半导体是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领域。1958年,我国就研制成功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然而,由于国家产业布局调整,我国的显示工业在60年代末已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这一时期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注重扩大工业规模即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但却忽略了或者说不得不牺牲了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即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1973-1974年的“蜗牛事件”。1970年,彩色电视技术“大会战”[16]拉开序幕。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考虑自国外引进彩色CRT技术。1973年,四机部组团赴美国康宁公司考察,临别时对方赠予蜗牛造型的玻璃工艺品,以展示其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怀有“慢慢走,一路平安”等吉祥寓意。然而,却有人以此为由,认为“美方污蔑辱骂我们爬行主义”,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做文章,技术引进工作被迫搁置,中国显示工业的发展进程再次受阻。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技术引进”。改革开放初期,在意识到工业的整体落后局面时,中国并没有及时、坚定地走向自主研发道路,而是转向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首先发生在了对于终端产品的直接引进上,而后又因为技术匹配的制约,慢慢向上游渗透,最终威胁到自主开发能力,原本可以保持的技术发展过程被中断。与此同时,曾经压抑的消费需求在该时段集中爆发,彩电成为消费热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彩电制造工业持续发力于技术引进而非技术开发,形成了区别于日韩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整机制造企业与彩管制造企业相对独立。又正是因为这样的产业结构,在后续全球范围内的彩管工业崩溃时,中国的整机制造企业才能够迅速转向,从CRT电视制造转至液晶显示电视制造。
四、
显示工业遗产的价值阐述
显示工业遗产的价值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
显示工业遗产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段该行业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时代背景、政策导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变化特征。
启动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显示工业,在60、70年代经历了由于产业布局调整、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导致的技术停滞,并在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浪潮中发展出独特的上下游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正是由于这样的产业结构,使得CRT整机制造企业并未受21世纪初的彩管工业崩溃的影响,迅速转向平板显示整机制造,而中国自主研发TFT-LCD的企业也在这一技术更新过程中成长起来。
因此,中国显示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从内史的角度来看,它集中展现了中国显示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轨迹,体现了CRT显示工业全面转向TFT-LCD显示工业的关键节点,也见证了TFT-LCD技术的本土化成长过程。从外史的角度来看,它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电子工业政策的客观映射,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20年内中国意图依靠“技术引进”发展民用工业,并由此中断的技术发展过程。
2.技术价值
工业遗产的技术价值常被误认为技术史价值,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技术史价值可大致对应历史价值中的内史价值部分,代表了某个地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技术发展水平,体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而技术价值则意指对于当下的技术研发和具体的生产活动具有的启发、借鉴或推进意义。认知技术价值的主体应为当下的“我者”,而非带入其它时空概念的“他者”。
对于技术价值的衡量,宜针对具体的认定对象进行提炼。如,京东方的TFT-LCD 五代线在终止其最初的LCD生产功能后,其产线技术直接推动了其他非LCD领域的技术发展,转而生产新的雷达天线和新型传感器产品。
此外,虽然难以对多个不同时空下的遗产进行具体的技术价值评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总结某一类遗产的技术/产业发展规律,以指导当下的技术研发和具体生产活动,这部分亦是重要的技术价值。譬如,中国显示工业遗产的整体技术价值,很大层面上体现于,它是液晶周期①的物质实证,可以指导当下的技术研发以及产业投资进入的时机。
3.其他衍生价值
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的诸多城市从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工业品的生产型城市。工厂的设立、工人居住空间的扩展,以及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福利设施制度的铺开,共同改变了城市的肌理。显示工业亦是如此,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厂房体量和职工数量迅速增长,切实影响了其所在城市的建设发展,重塑了城市肌理。[17] 根据《下塔吉尔宪章》和《无锡建议》[18]的定义,工业遗产包括直接的生产空间、输送和利用的场所,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对于迭代迅速的显示工业来说,这些社会活动场所的存续时间,往往还要长于其最初服务的工业生产空间,可以为当下社会学、城市规划研究提供珍贵样本。
显示工业遗产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大尺度的生产空间适宜改建成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而其它的附属社会活动场所,除存续利用之外,也可改为它用,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收益。如,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1989年投产,2009年关闭,原工业园区被改造为恒通国际创新园区。原车间厂房改建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5年竣工开放,仅2019一年就设立9项临展,并持续举办“语冰讲堂”、“MS童乐园”等多项系列公益活动;原办公楼改建为北京明德医院;原员工宿舍改建为和颐酒店。园区总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年产值近400亿元,人均劳动生产率近800万元。[19]
五、
余论
从原初的生产对象来看,中国显示工业遗产主要涉及到两种类型:CRT生产线及其相关遗产、TFT-LCD低世代生产线及其相关遗产。前者的数量较多、分布较为广泛,其始建年代集中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八大彩管厂”为代表。受到平板显示技术的冲击,大量产线已陆续关停,仅个别产线仍在生产特种产品(如长沙LG·曙光),少部分转为其它工业生产功能或改作其它非生产功能使用(如前述北京·松下彩管厂)。
这些以不同的状态延续至今的显示工业遗产,集中展现了显示技术的发展轨迹,见证了中国显示工业生产流程的变革,反映了相关生产关系的变化,对技术史、工业史、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显示工业遗产亦可作为物质载体,直观地向民众展示中国显示行业从无到有,从曾经受制于人到今日位居世界前列的成长过程,提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指导我们更加坚定地走自主研发的道路。
然而,越来越多的显示工业遗产,在尚未进入文化遗产学视野之前,就已经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相较于其它文化遗产类型,显示工业遗产的存续时间较短,距离城市核心区较近,不论在时间维度上还是空间维度上都更为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无意识地忽略它们的变化,致使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在了昨日的“无视”之中。笔者谨以此文,在明晰其本土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试论以显示工业为代表的电子工业遗产的价值,企盼这部分见证工业发展重要进程的遗产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并期待后续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附记:本文得到北京大学孙华教授、中国科学院欧阳钟灿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潜伟教授的指导与支持,谨此致谢。
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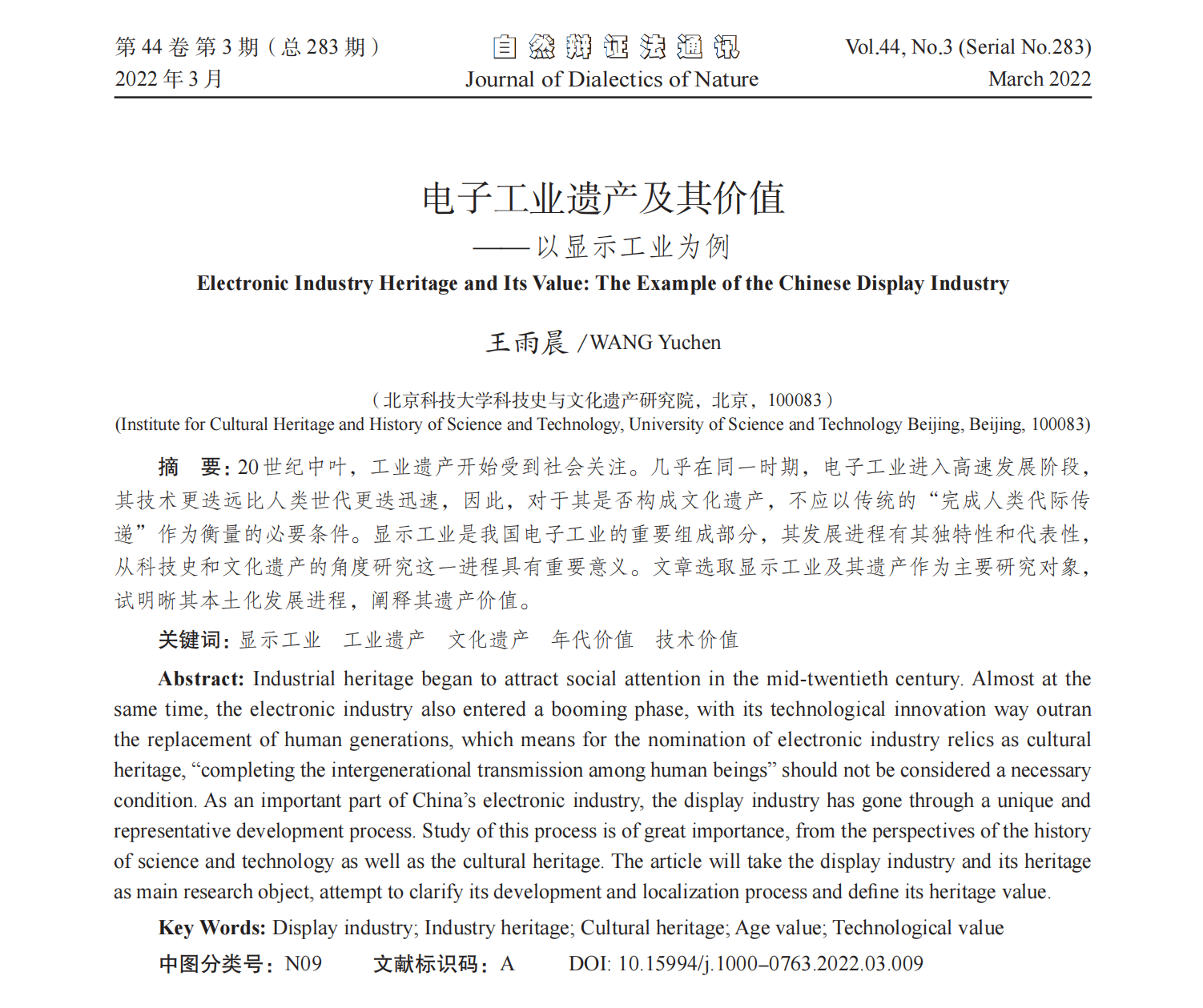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雨晨,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

